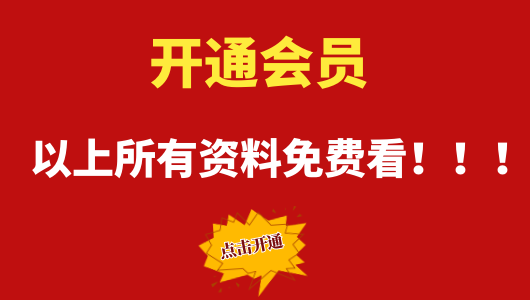一、为什么做民间宗教研究?
理由1名词解释:
中国民间的宗教文化渗透于大众的生活之中,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,民间宗教传统不仅影响着占中国社会大多数的一般民众的思维方式、生产实践、社会关系和政治行为,还与帝国上层建筑和象征体系的构造形成微妙的冲突和互补关系。因而,民间宗教的研究,不仅可以提供一个考察中国社会-文化的基层的角度,而且对于理解中国社会-文化全貌有重要的意义。
理由2名词解释:
改革以来,随着意识形态控制的逐步松懈,在全国的许多地区民间的传统社会-文化形态出现 “死灰复燃”的现象。民间宗教信仰活动就又一次重新兴盛起来,丁荷生(Kenneth Dean)1993年发表的调查说,仅福建一个省,到1992年就重建了三万多个神庙,而各个大的家族还在陆续重建或新建他们的祠堂。
传统民间信仰的基本形式依然顽强地传续下来,并且仍旧是一般民众的信仰主要的表达与实现方式,比如请大仙、信卜筮、看风水、讲禁忌等等以及敬造庙宇、供奉神像、岁时祭祀、举行庙会,各种仪式和方法与1949年以前完全一样。
理由3名词解释:
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里,中国社会科学界曾采用古典进化论的分类架构,简单地把丰富的民间信仰、仪式和象征形式归结为古代史的残余,在还没有对它们加以深入的探讨之前,就认为这些文化形式在社会进入“现代”之后就不再具有原有的功能和意义。为了解释这种旧传统的复兴“现象”,政策研究界采用“社会主义初级阶段”的理论,以中国社会还未进入高级社会主义阶段为理由、解释目前民间“迷信”存在的时代特点和它为什么尚未“消失”的缘由。
随着研究的展开,学术界逐渐认识到,有三方面合力促成民间宗教的复兴——
内在原因名词解释:
民间一直需要支持信心与精神的信仰,民间宗教信仰在平民思想中始终不绝的延续。在没有真正的文化提升之前,支撑信心的信仰及其形式,终究要由隐而显。
外在环境名词解释:
1、由于对宏扬传统文化、发扬爱国主义的意识形态的误解;2、观光旅游形式为主的“文化搭台、经济唱戏”的需要。
研究还需要进一步深入。
二、民间宗教研究的内容(研究些什么?)
一、什么是民间宗教?
1、传统社会的看法名词解释:
淫祀与秘密教派。
传统的地域民间节日,一般会以寺庙为中心,举行酬神、娱神、求神的群众性集会,同时也举行娱乐、游冶、集市等活动。这种群众性的文化活动中常常表现出纵欲的、粗放的、显示人的自然本性的行为方式,维护传统社会秩序的等级制度被极大地冲淡了。这类活动的组织者往往是社会上层人士,诸如城市的士绅或商人,乡村的大户和族长,主要的参加者则是下层民众,甚至平时饱受禁忌的妇女也不再限制地参加庙会及娱神演出。在此期间使用的各种服装、道具等象征物品表现了对“官方符号系统”的嘲弄,而且极尽铺张浪费之能事,对传统社会的统治秩序具有强烈的颠覆性和破坏性。
因而,它常常被官方目为淫祀,而遭到禁止。
秘密教派。白莲教、明教,天地会、三合会等等。
2、现代学术界看法主要包括两类名词解释:
一类不承认民间的信仰、仪式、象征为宗教;另一类认为它们构成一个“民间宗教”。前者为采用古典宗教学的分类架构的学者。他们认为,因为民间的信仰没有完整的经典和神统、仪式不表现为教会的聚集礼拜、而且象征继承了许多远古的符号,所以不能被当成宗教与基督教、伊斯兰教、佛教等制度化的宗教相提并论,也不能与中国大传统里的儒、道、释三教等同待之。
后者为对于社会-文化人类学者。他们之所以采用这一概念,是因为他们主张通过对民间的信仰、仪式和象征的宗教体系的考察,探讨中国社会中的文化现象与社会现象之间的关系。具体地说,他们所理解的“中国民间宗教”指——在中国一般民众、尤其是农民中间的(1)神、祖先、鬼的信仰;(2)庙祭、年度祭祖和生命周期仪式;(3)血缘性的家族和地域性庙宇的仪式组织;(4)世界观和宇宙观的象征体系。
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,传统的信仰、仪式和象征不仅影响着占中国社会大多数的一般民众的思维方式、生产实践、社会关系和政治行为,还与帝国上层建筑和象征体系的构造形成微妙的冲突和互补关系。因而,民间的信仰、仪式和象征的研究,不仅可以提供一个考察中国社会-文化的基层的角度,而且对于理解中国社会-文化全貌有重要的意义。
二、民间宗教体系
这一文化体系包括信仰、仪式和象征三个不可分开的体系名词解释:
信仰体系主要包括神、祖先和鬼三类;
仪式形态包括家祭、庙祭、墓祭、公共节庆、人生礼仪、占验术等等;
象征体系包括神系的象征、地理情景的象征、文字象征 (如对联、族谱、道符等)、自然物象征等等。
三、民间宗教与国家传统
所谓“民间宗教”只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而不代表它的整体。它不仅与官方和士大夫的文化体系有差别,与制度化的儒教、道教和佛教也不可混为一谈。如果我们采用“大传统”和“小传统”的概念的话,那么我们就会发现民间宗教属于“小传统”(尽管信仰或实践这种宗教的人占中国人口的大部分),与作为“大传统”的官方文化、儒、道、释文化之间存在许多差异。
例如,“大传统”比较制度化、有文字的系统化记载、受官方的承认和利用、离一般民众的生活实践较远、受上层社会的支撑等等;而民间宗教则比较弥散、口头传承比文字传承优先、不受官方承认、与一般民众的生活实践不可分离等等。
总之,第一,民间宗教和“大传统”之间的关系十分复杂,并且两者各自的内部都存在不同的层面和分化。第二、民间宗教是在与 “大传统”的不断互动和交换中发展的。第三,在这种互动和交换中,民间宗教始终没有失去它自身的社会-文化特点。
历史学家最为关注的是第二点,民间宗教与 “大传统” 不断互动和交换。在他们看来,民间宗教不但是一种象征,同时也是改变社会文化网络历史过程的动力。
四、民间宗教与区域社会史 民间宗教如何与区域社会发生关系? 家神——角头庙——村庙——超村际的庙宇 民间祭祀组织与区域社会结构发展。
五、祭祀圈理论及其修正名词解释:
最早提出祭祀圈概念的是日本学者冈田谦,后来参与台湾中央研究院“浊大计划”的人类学者,根据浊大流域的田野调查资料再度提出祭祀圈的观念,并试图建立祭祀圈的模式。这个模式是有点回应Skinner的市场体系概念。当时Skinner的学生Crissman,曾将市场体系运用在彰化平原二林的实证研究,结果发现市场体系理论不适用於解释台湾汉人社会。因此,台湾学者认为:或许可以从祭祀圈,亦即从村庙祭神的角度,不必再从市场体系来看聚落的空间分布及其发展模式。也就是企图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探讨汉人的活动空间、人群的地域组织及社会动作等问题。
台湾学者一般认为,“祭祀圈”是指特定地域范围内的公众祭祀组织。因而亦可定义为以神明崇拜为标志的地域性社会组织。这种地域组织通常以聚落或村落为基本单位,逐渐向超村落区域扩展。
由於两岸学者自改革开放以来交流频仍,在台湾本土形成的理论也有机会传播到对岸。诸如刘永华、郑振满以及王铭铭等人的研究,对於祭祀圈名词定义以及范围的界定,略作修正,并提出更具弹性且涉及宗教与文化现象的探讨。
在大陆传统社会的区域研究中,大陆学者同样发现“祭祀圈”此类地域组织的普遍存在,但其社会性质未必“完全是老百姓的自发性组织”。从里社向村庙演变的历史过程,固然可以视为地域社会的自我组织过程,但也不能忽视官方意识形态与政治体制的制约。只有把 “祭祀圈”置于更为广阔的历史背景之中,才有可能阐明其社会性质和历史成因。
丁荷生(Kenneth Dean)在福建甫田地区进行的区域仪式体系之研究,也认为祭祀圈的概念尚不足以概括这个历史过程的复杂性,应该将国家、区域、地方的文化体系视为一种开放而不是封闭的体系,而且不同层级之间的体系是有互动关系的。